 論文專著:
論文專著:

發表論文40余篇,其中在《光明日報》、《教育研究》、《人民教育》、《全球教育展望》、《學科教育》、《大學物理》、《物理實驗》等權威或核心期刊上發表13篇,正式出版專著2部、譯著2部。
 出版專著:
出版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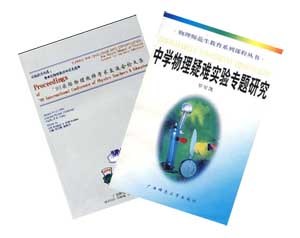
1、《物理教育研究》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中考命題指導•理科》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
3、《科學探究與國家科學教育標準——學與教的指南》 科學普及出版社 2004
4、《2004年中考命題指導叢書•綜合理科》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4
5、《(普通高中新課程研修手冊)學校課程方案的形成與學生選課指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6、《探究——小學科學教學的思想、觀點與策略》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7、 "TURNING THE CHALLENGE INTO OPPORTUNITIES: the Historic Mission of Physics Teacher for the Next Millennium-Proceedings of '9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Physics Teachers & Educator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9國際物理教師學術交流論文集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0
9、《中學物理疑難實驗專題研究》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8
 發表論文:
發表論文:
英文:
1. Luo Xingkai(羅星凱), Liu Xiaobing(劉小兵) etc., Teaching Science with Thought-Provoking Hands-on Experiments, (泰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校內外科學實踐活動國際研討會"大會報告,1999/12/13.
2. Luo Xingkai(羅星凱), Liu Xiaobing(劉小兵) etc., Educational Considerations for Designing, Selecting and Using Hands-on Experiments, (德國)國際物理實驗教育會議大會報告(Duisburg/Germany, 25/8/1998), 全文收入論文集"B. Born, etc., HANDS ON-EXPERIMENTS IN PHYSICS EDUCATION - ROCEEDINGS, 75-81 (ISBN 3-00-004409-4)
3. Luo Xingkai(羅星凱), "Educating Prospective Physics Teachers for a Changing World in China--Program Innovation & Practice at GNU", in the Changing Role of Physics Departments in Modern University--Proceedings of ICUPE, A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 399/College Park (USA), 649-658(ISBN 1-56396-698-0) 1997.
中文:
1 物理教育里面有真正的學問——記趙凱華先生對我的學術影響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期刊】大學物理 2010-05-15
2 學生面對情境性試題為何如此失常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人民教育 2010-06-03
3 從學科教育到科學教育——我的學術之路與顧明遠教授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物理室 【期刊】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02-15
4 世界杯熱賽中談科技與科技教育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福建論壇(社科教育版) 2006-09-20
5 有理的科學知識被無理地“驗證”——從理科教學中實驗結果與理論的不相符談起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人民教育 2007-04-03
6 大學與中小學教師教育合作伙伴關系建設:理念與行動 鐘瑞添; 耿娟娟;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廣西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與電子工程學院 廣西桂林; 廣西桂林 【期刊】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10-15
7 概念轉變理論及其發展述評 吳嫻; 羅星凱; 辛濤 廣西師范學院物理與電子科學系;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北京師范大學發展心理研究所 【期刊】心理科學進展 2008-11-15
8 論科學教育研究與科學教育改革 丁邦平; 羅星凱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教育研究 2008-02-15
9 中學生科學假設質量評價量表的制定 羅筑華;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教育科學 2008-06-20
10 小學科學教育里的大學問——圍繞《一堂“失敗”的好課》展開的一次參與式培訓 羅星凱; 吳嫻; 趙光平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人民教育 2003-11-25
11 新課程中考走向④理科中考:從2004看2005 羅星凱; 曾平飛; 趙光平; 劉小兵; 薛躍規; 吳德漢; 唐力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理科; 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理科 所長、教授、教育部初中畢業學業考試評價理科研究組負責人; 項目組核心成員 【期刊】人民教育 2005-05-18
12 “科學大眾化”的困境:社會學的分析 魏冰; 羅星凱 廣州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東廣州; 廣西桂林 【期刊】外國教育研究 2005-06-20
13 美國基礎科學教育改革及其主要特點——兼談加強我國科學教育研究 丁邦平; 羅星凱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北京 【期刊】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08-20
14 新課程背景下中考怎么考③ 新課程:“雙基”和“探究”如何考——關于科學學科中考走向的研究與思考 羅星凱; 劉小兵; 曾平飛; 趙光平; 薛躍規; 黃都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全國初中畢業升學考試科學學科評價課題組負責人 【期刊】人民教育 2004-05-03
15 從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看基礎教育的問題——張澤院士訪談錄 楊宏艷; 許家雄;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桂林; 廣西桂林 【期刊】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03-20
16 開放探究就是開放思維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所長、教授 【期刊】人民教育 2004-07-18
17 一個“出乎意料”的問題引發的探究活動 劉小兵;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物理教育研究室;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物理教育研究室 廣西桂林; 廣西桂林 【期刊】學科教育 2004-11-25
18 一項關于低年級兒童速度概念發展的研究 吳嫻; 趙光毅; 羅星凱 廣西師范學院物理系;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南寧; 廣西南寧; 廣西桂林 【期刊】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03-20
19 高中新課程:學校多元化發展的平臺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課程研究中心 【期刊】全球教育展望 2003-09-15
20 實施科學探究性學習必須正視的問題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全球教育展望 2004-03-15
21 課堂演示實驗在科學教育中的非語言傳播作用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電子系 【期刊】學科教育 1997-05-25
22 一個可用于機械波教學的人類視覺局限演示器的設計與制作 易其順; 羅星凱 廣西南寧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物理系;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電子系 【期刊】物理實驗 1998-12-15
23 深化物理教育研究,切實提高學與教的質量──我們的思考與實踐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系 【期刊】大學物理 1995-07-10
24 用一個簡單的裝置演示邁克耳孫-莫雷實驗所期望的結果 V.M.Babovi; B.A.Aniin; D.M.Davidovi;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 【期刊】大學物理 1992-08-28
25 課程專家就教師關心的問題答本刊記者問(三) 透視科學探究性學習 余慧娟; 賴配根;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 本刊記者; 本刊記者 【期刊】人民教育 2002-09-25
26 “密度概念的引入”探究性教學設計 羅星凱; 劉小兵; 梁維剛; 吳嫻; 張琴美; 李萍昌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人民教育 2002-09-25
27 一堂“失敗”的好課 趙光平 ;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期刊】人民教育 2002-10-25
28 光通信演示實驗裝置的設計與制作 韓長明; 梁維剛; 劉小兵;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與電子科學系;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與電子科學系 【期刊】物理實驗 2000-12-25
29 新型水波干涉儀 劉小兵; 梁維剛; 羅星凱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系;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系; 廣西師范大學物理系 廣西桂林; 廣西桂林 【期刊】物理實驗 2001-11-25
資料更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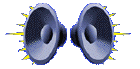 媒體報道一:
媒體報道一:

理科教學中如何實施科學探究性學習?
——訪教育部廣西師范大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羅星凱博士
探究性學習≠研究性學習
問:我們注意到,在新課程中,特別強調學生自主探究。請簡要地告訴我們什么叫做探究性學習?它與研究性學習是不是一回事?
答:簡而言之,探究性學習是與接受式學習相對的,它是一種在好奇心驅使下的、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生有高度智力投入且內容和形式都十分豐富的學習活動。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活”和“動”兩個字。“活”一方面表現為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表現為學習活動的生成性。教室里實際所發生的一切不可能都由教師所預設,學生的思維常常迸發出令教師意想不到的智慧的火花;“動”表現為學生真正的動手操作、動眼觀察、動腦思考。從本質上看,它和研究性學習沒有什么區別。然而,在新課程中,研究性學習的實施是通過綜合實踐活動這樣一種特殊形態的課程來進行的,而探究式學習則是貫穿于各學科課程標準和教材之中的。
科學探究:改變學習方式的突破口
問:為什么理科各學科的國家課程標準要把科學探究置于核心地位?
答:我想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理由。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性的科學教育改革風起云涌。無論是人類所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國家間日益激烈的國力競爭,還是學校教育的現狀,都促使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中小學教育,特別是科學教育的加強和改進。通過優質的基礎教育特別是科學教育提高全民的科學素養就成了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謀求發展的戰略。我國在新一輪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特別強調學生學習方式的改善,在理科各科的國家課程標準中,將科學探究作為核心,是科教興國戰略在理科課程改革中的具體體現。
此外,本次課程改革的核心目標是實現課程功能的轉變,就是要改變課程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強調形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使獲得知識與技能的過程成為學會學習和形成正確價值觀的過程。實現這樣三位一體的課程功能,探究性學習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載體。好的探究性學習活動,通過富有啟發性的問題、或能激起問題的事物或現象,驅動學生積極主動地進行觀察、實驗、收集事實證據、提出和求證假說、做出解釋等建構知識的活動,通過交流、辯論,使學生不僅能擴展自己對知識的理解,而且能提高質疑、推理和批判性地思考科學現象的能力。通過“做”科學,學生既能學到知識,又能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同時形成正確的科學態度。
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來自人們對學生如何學習科學的認識。對于不少科學知識內容,親歷探究是真正體驗科學之魅力的最好途徑。
理科課程突出科學探究的學習方式,旨在讓學生通過手腦并用的探究活動,學習科學知識和方法,增進對科學的理解,體驗探究的樂趣。
選擇核心內容讓學生探究
問: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探究式學習在貫徹中遇到諸多問題,一方面教材中如何真正體現這一新的理念,一方面如何在有限的課時內完成探究過程,還有教師如何給以恰當的引導。對此,你怎樣看?
答:在義務教育理科的國家課程標準中,科學探究既作為科學學習內容,又作為科學學習方法出現,目的在于通過親歷科學探究活動,讓學生既學到科學知識,又培養科學探究能力,同時增加對科學探究的理解。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時間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探究學習的確需要更多的時間。然而,在這個問題的理解上普遍存在誤區,那就是我們往往是靜態地、孤立地計算探究性學習所花費的時間,而沒有考慮學生真正掌握知識為日后的學習所省下的麻煩。事實上,從學生真正理解的角度來計算,那種“堤內損失堤外補”的辦法反而是效率更低的。
談到時間的問題,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那就是探究性學習的選題。學科教學中選擇探究性學習的內容自然要依據課程標準,但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將所有的內容都設計成探究性的。最值得選擇的內容,應該是對于學科來說具有核心和基礎地位的那些概念和規律性知識,因為學生真正理解了這樣的知識,就等于掌握了學科知識的主干,形成了擴充和擴展自己知識結構的能力。在這樣的知識的學習上,多花一點時間是沒有多大爭議的。
教師應當是“向導”而不是“看守”
問:這么看來,時間不應該成為阻礙科學探究性學習實施的障礙。不過,教師在探究性學習中的作用是另一個棘手的問題。許多人感到探究性的課堂很不好控制,我們也看到一些探究課顯得亂糟糟的。而有人認為,“亂”說明學生活動起來了,這正是新課程理念的反映。對此,你怎么看?
答:首先,如果認為課堂的一切都要在教師的掌握之中,教師失去對課堂的控制就意味著教學的失敗,這就涉及到觀念轉變的問題了。既然探究性學習是學習者自己理解和發現世界的過程,教師的角色就應該是這種過程的促進者和引導者。因此,探究性科學教學需要從根本上重新考慮教師和學生的關系。如果我們承認學生是有思想、有頭腦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由教師操縱的機器,那在課堂上要刻意謀求的就不是控制課堂,而是如何引領學生探索知識的奧秘,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對于學生來說教師應該是guider(向導)而不是guarder(看守)。
解決了觀念的問題,技術的問題同樣棘手。我曾經聽過這樣一堂課,教師在不到10分鐘的時間內,先后組織了學生的小組討論和跨小組的討論。學生真可謂“動”起來了。可是,學生是怎么“動”的?又“動”了些什么呢?我們看到的是小組討論時,每個人都在高聲地說,誰也聽不清誰。而剛剛討論不到5分鐘,學生又要進行跨小組的討論。這樣,大量時間都花在了體現“小組之間也有交流”的形式上了。其實,科學探究真正要強調的是“動腦”,學生肢體上的“動”、嘴巴上的“動”,最終都是為了更好地、更積極地投入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是“行動不如心動”。談到這里,我特別要指出的是,盡管科學探究性教學中,不能老是牽著學生的思維沿著教師預設的軌道行進,但探究性教學決不等于課堂上的雜亂無章,而應該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教學活動。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問題、一個針對性強又富有挑戰性的任務提出后,課堂上可能很寂靜,但此時學生的頭腦也許“動”得是最激烈的。
探究性教學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教學活動
問:探究性教學實際上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教學活動,聽您說來確實如此。不過這樣是不是會與探究性學習的開放性、自主性、生成性相矛盾?
答:教學活動被“精心設計”之后,怎么能保證“開放性”、“自主性”和“生成性”呢?這似乎有矛盾。但實際上,不管是問題的“開放”、學生的“自主”,還是課堂上教與學的“生成”都不是目的,我們最應該關注的應該是教室里實實在在所發生的學生的學習活動,我們最終所追求的也正是學生學習活動的質量。因此,我們不僅要關心課堂“開放得如何”與“生成得如何”、學生“自主得如何”,還要計較課堂是“如何開放”與“如何生成”的,學生又是“如何自主”的,更不能不管課堂“開放了什么”與“生成了什么”、學生“自主學習了什么”。因為新課程所提倡的科學探究性學習承載著科學知識的掌握、科學探究能力的發展、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習慣的培養等多重任務。正是這樣的任務決定了“探究性教學實際上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教學活動”。
科學探究并不神秘
問:這么說來,推行科學探究性學習確實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針對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您認為要特別加強哪些方面的工作?
答:人類與生俱來具有探究的本能,探究的過程是由一個人的好奇心、求知欲或要理解觀察到的內容、解決一個問題的熱情所驅動的。不應該神話科學探究,我們沒有必要糾纏一堂課是否完整地經歷了探究的幾個環節,在每一個環節學生是否達到了自主探究的程度;也沒有必要刻意去追求學生在程序上、形式上是否重復科學家發現的過程,我們真正關注的是學生的“學”。如果探究的環節都有了,探究的程序也都走過了,科學家的樣子也做得像模像樣了,學生的學習卻仍然是機械的而不是有意義的,那樣的探究又有什么真正的價值?
另外,探究性學習需要教師為學生營造一個寬松、民主、和諧的課堂學習環境,學生的想法即使與標準答案不一致也應得到理解和尊重。沒有一個有利于教學創新的課堂教學評價環境,在那種刻板僵化、追求形式、面面俱到的課堂教學評價模式的壓力下,很難想象一個教師在課堂上會真正聚焦于學生實際的學習生活、教室里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的質與量。
來源:《中國教育報》2002年11月28日第3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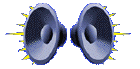 媒體報道二:
媒體報道二:

一位大學教授的基礎教育情結
實事求是地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造就了一批“名人”。
不少師范大學的教授、學者,幾年內都成了炙手可熱的“課改專家”。風云人物此起彼伏。兩個過去相對隔離的世界因為這批教授、學者而擴大了交合。
但羅星凱算不上這個名氣圈里的“大腕”。
他不是哪個學科課程標準組的負責人,也很少見他在新課程通識培訓的大講臺上露面。
他負責的是那個實驗面積最小、難度最大的《科學(7~9年級)》課程的“專業支持”工作。涉及的教師、學生數相比之下顯得微不足道。
不過,只要是實驗區聽過他的課、與他交談過的人,也許不知道他從哪里來,甚至記不得他的名字,但是卻記住了科學探究是怎么一回事。
他走過的課堂,總會留下點什么,總是能讓人心靈為之震服。
他由此而“小有名氣”。
“給教師以理解和真正的支持”
“現在我們倒是重視過程了,但一些教師往往把握不住。學生本來說錯了,老師卻還不知道。我看自己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不要耽誤了這一代孩子!”
在實驗區的一次課后研討活動中,某“指導者”的一通話,像機關槍一樣把老師們射懵了。
羅星凱教授有點坐不住了。
“聽了這位老師的話,我也想談談自己的感受。應該說,您講的現象是存在的,我們在聽課時也常遇到這樣的情況,這的確需要認真對待。但如果我們將問題歸咎于‘重視過程’,可能就要打一個問號了。
“我現在反問一下:教師還是一樣的教師,為什么以前問題沒這么嚴重?是怎么造成的?實際上以前教師也有不懂的,但是他的課堂是封閉的,沒有給孩子多少說話的機會,自然也沒有教師犯錯誤的機會。現在課堂開放了,問題出現了,我們就認為是老師的過錯,甚至給他一頂‘耽誤一代孩子’的帽子!這個帽子誰頂得起?教師在課程改革的實踐中壓力已夠大了,他們需要理解和真正的支持!”
全場一片寂靜。
座談一結束,老師們就圍了上來,許多人握著羅星凱的手,聲音哽咽。那是一種被人理解的激動。
“什么樣的人最適合去進行探究性教學?是他自己被這樣的方式教過的人。但是我們的老師中有誰是被這樣的方式教過的?所以我們首先應該給教師們的是理解而不是指責。”
2002年5月,羅星凱與同事趙光平博士聽了一堂小學科學課。課后,上課老師的第一句話就是:“這節課該講的都講了,該做的也都做了,可學生還是不會。真對不起,讓你們聽了一堂失敗的課。”顯然,她做好了“挨批”的準備。沒想到,羅星凱卻說她上的是“一堂‘失敗’的好課”,因為老師與學生之間有真正的對話交流,學生真實的想法和理解上的困難得以自然地展現。
這一案例曾在一個網站上引發了強烈的反響,焦點是他們對上課老師的評價。“這多少令我感到有點意外,因為在我們看來,這樣的評價是很自然的。不過這也說明,教師在嘗試新課程中太需要寬松的評價環境了!”說這話時,羅星凱一臉的認真。
“我們沒有特別的本事,
就是比較能把問題說到老師的心坎上”
“站著說話不腰疼,有本事你來上節課給我看看!”這樣的話或者這樣的情緒,因為一個問題評得不到位,而從上課教師口中噴涌出來,弄得火藥味兒十足,也是常有的事。
“我慶幸,自己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情景。”羅星凱教授對我說,“因為我總能夠設法讓老師們折服。”
羅星凱所說的“折服”,并不總是靠給教師“打氣”來實現的。
2003年11月,深圳某學校一節初中科學課,有100多位教師在現場觀課。
那節課講的是“內能的變化”。為了讓學生對做功轉化為內能有所體驗,上課的老師花了很多時間讓學生做活動。比如,用手彎曲鐵絲、用鋼鋸鋸鐵絲和木筷、用砂布摩擦鐵絲等等。實驗非常成功,最后學生對現象的解釋也沒有困難。
老師們都很滿意,認為很好地體現了學生的主體地位,重視知識的形成過程,在學生已有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學習新知識,并用所學知識解釋生活中的實際問題。學生學習知識的過程中充滿樂趣。這些正是新課標所要求的。
羅星凱沒有說話。
這時,有人提到科學課時不夠用的問題。羅星凱覺得是個好時機,于是用他那一口帶著較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徐徐講開了:
“課堂上讓學生彎鐵絲等很多類似的活動,花了很多時間,都是為了說明這樣的操作‘可以產生熱’。但這是用一句話就可以喚起的生活經驗,一定要這么費時費力來重復嗎?
“學生在學習‘內能的變化’時,并不缺乏‘摩擦生熱’這類的經驗。真正的困難在于,他們說的話和你科學上的表達不一樣。這里是做功了,那兒是發熱了,怎么就是內能變化了呢?這個東西他不懂,而在這上面老師幾乎就沒有花時間去解決。換句話說,學生不困難的東西,你拼命地讓他去體驗、去做,而學生真正有困難的地方你沒有去給他搭橋,讓他的認識提高,使生活經驗提升為科學認識。所以我認為這樣的教學就是低效甚至無效的勞動。如果能多剔除這樣的勞動,把勁兒用在該用的地方,我們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就能提高了。”
他那平和的表情下,竟然“綿里藏針”,一下就扎出了血。
可是,誰又能說沒有道理呢?
他那認真勁兒不容人質疑他學術研討的誠意。
半晌沒有人說話。
不久,掌聲響起。
“這個問題其實很典型。”羅星凱對我說,“為什么有些人不認同新課程?如果說這樣的熱鬧、活動就是所謂的注重過程、強調體驗,那么,別人就會以為,哦,原來新課程就是要弄這些東西呀!這就是新課程啊!有眼光的老師肯定不會認可。這樣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就像我們用力一拳打出去,一定要打準地方一樣,否則,自己反而會摔倒。我們確實應該肯定老師們追求新課程理念的勇氣,但是問題也一定要指出來,而且要指出問題的癥結。”
“您講得這樣尖銳,會不會傷了老師們的積極性?”我擔心地問道。
“實際上,我們這樣講了以后,老師們很服氣呀。只要你準確地指出問題,很平等地和老師們探討,就不會存在什么表揚就高興、指出問題就不高興的事情。你知道嗎,老師們其實是非常渴望有人能幫助他們解決教學中的實際問題的。”
《科學(7~9年級)》課程的推進涉及到的問題很多。羅星凱和他的團隊在2003到2005年里,曾經數十次深入課堂,所跑實驗區大大小小的學校不下20個,聽課上百節。
“但我們畢竟只是專業支持工作組,只是一個學科的研究者、不斷的思考者。我們沒有特別的本事,就是比較能把問題說到老師們的心坎上去。”
“你別看不起這個!”
“把問題說到老師們的心坎上去”,對久居象牙塔的大學教授來說,并不容易。
過去師范大學與基礎教育之間的“隔離”狀態,其實很難說會因為一場課程改革而親密無間。
因為“隔離”的根本原因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
“1985年,我考上江西師范大學物理教學法研究生的時候,還很猶豫要不要去讀。在我們當時學物理的人印象中,有本事的人一般不會去學物理教學法,只有理論物理才算是物理,才上檔次。后來想一想,自己當時在中學當老師,考一次不容易,就去了。”羅星凱這樣回憶說。
其實,即使是現在,學科教學法也還是大學里不怎么排得上號的領域。
更要命的是,那些具有“實踐關懷”的東西,在大學學術評價體系里,幾乎都是上不了臺面的。
“誰會愿意沉下心來,去中小學做什么案例研究呢?且不說你這個研究本身能不能做下來,在這樣的環境里,又有多少人能不顧一切地堅持走下去呢?”羅星凱嘆了口氣。
理論是理論,實踐是實踐。任憑中小學教師指責理論的無用,大學自有自己的活法。
羅星凱慶幸自己做了這個大流中的成功叛逆者。
“在我國召開的首次物理教育國際會議上,上研二的我接觸到了很多在物理學研究上很有成就的物理學家,他們對物理教育也很有興趣、很有研究。這給我的影響不小。
“當時我覺得別人這么重視總是有它的道理,但是究竟是什么道理,我那時還沒有完全琢磨出來。”
1988年,他來到廣西師范大學工作,專門從事物理教學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因為有那些國際大家的影響,他并沒有因此看低自己。
“當你做得好一點的時候,學生會給你一個回報。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那時候,羅星凱還發現,即使是在桂林那樣的中等城市,老百姓上好學校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
“如果一個社會對于教育只有量的需求時,你去研究怎么把它教得更好,那有什么意義呢?只有當有了質的需求的時候,教學研究才有意義。因為好的教育肯定需要有好的研究做基礎。
“你想一想,你要教一門學科,首先你得自己學得比較好吧。然后,你要把知識去教給人,而這個人本身太復雜了。關于人的學問,關于人怎樣學習知識、形成能力、培養情感的學問,實在是太深奧了。國外那些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都愿意來做這件事情,一點也不奇怪。
“所以,你別看不起這個東西。你即使再有才華,讓你一輩子來做這件事情,也不一定能做好,能產生很好的實際效果。所以,我覺得,我以后一輩子來做這件事情,也不屈才,也值。不會后悔了!”他顯得有些激動。
“你的態度有時候就決定了別人對你的看法”
在社會大環境里,個人往往是渺小的。
但如果自己也認為自己渺小,那就真的渺小了。
“越是別人瞧不起的行當,越是要做出點成績來。不然,你真的就如別人所認為的那樣了。”
直到這次采訪,我才知道,他在參加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工作之前,已經有多項研究成果獲得國家級、省級獎勵了。
“如果不是這樣的信念,也許我早就半途而廢了。”羅星凱回想起來,很感謝自己當初那股“拼命三郎”的勁兒。
課程改革四年里,書店里關于新課程的書籍種類與數目每年幾乎都以幾何級數增長。
羅星凱卻幾乎沒有出一本個人寫的課程改革方面的書。
他有的只是幾篇案例和為數不太多的學術文章。那是他認為“真正拿得出手”的東西。
《一堂“失敗”的好課》是他和他的同事發表的一篇現場案例研究的文章,當時在中小學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討論文章紛至沓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太真實了。
人們總是習慣了將近乎完美的課例予以公開,習慣了公開的都是正面的評價。
當真正讀到可能就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課例,讀到可能就是自己常犯的錯誤時,怎么會沒有共鳴呢?而討論中,羅星凱和他的同事們與上課老師的平等對話,將各種重要認知理論活靈活現地蘊藏其中,使得研究不僅僅是一個實踐呈現,更有了思維厚度,有了理論深度,令人回味無窮。
“可是,學術界卻不一定這么認為。有人一看題目,就覺得,一堂課還有什么太大的研究檔次和水平?
“我不能左右人家的評價,但我始終覺得,做了一個研究出來發表,就像丟了一個東西,如果一點響聲都沒有,你說你的檔次很高,又有什么意義呢?就是遭人罵,也得有人來罵才好啊!”
羅星凱依舊堅信,自己到中小學課堂做研究“沉淀”出來的這些案例都是好東西。
“但是,也有大學里的同行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它的價值。本校一位資深的化學教授看了以后,專門來找我說:‘我都看得入迷了。你這個研究案例很像MBA的那些經典案例。將來教育也會像MBA培養商業人才一樣,需要這樣的案例作為教學的支持。’”
一席話,道出了羅星凱的心聲。他感到了被理解的厚重。
“其實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他們知道你在別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上面花那么多力氣,而且那么執著,他在佩服你這個人這種態度的同時,也就認可了你的工作。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一個人做成功一件事情,我們認為是因為這個人特別聰明,或者運氣特別好。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對這個事情的態度,決定了他會怎樣去投入它。有投入就有回報嘛!特別是當人家不太容易自動地認可你這個學科的時候,你的態度就決定了別人對你的看法。
“所以我們的很多領導、同事逐漸認可我們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是我們做事的認真態度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羅星凱抽身參加課程改革的事,得到了廣西師大的大力支持——來去自由。
“說實話,搞課程改革,需要投入的時間太多。你若每次出來,要這個批準、那個同意,還有一些人對你說三道四的時候,是很容易打‘退堂鼓’的。好在我的領導和同事都比較寬容我,他們相信我不會去搞什么只顧自己的事。”
他成功地擺脫了大學教授參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諸多煩惱和羈絆。
現在,由他任常務副主任的教育部廣西師范大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無論軟硬條件,還是業績和口碑,都是國內屈指可數的。
這是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的。
信念,有的時候就這么神奇。
“尋覓一種終極的動力和寄托”
羅星凱并不愿意將自己如此投入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事情,描繪成多么高尚的行為。
“我其實是有自己的‘功利’追求的!”他嘿嘿一笑,一臉的坦誠。
在參加課程改革之前,他與中小學的接觸是非常有限的。“至少人家不會像現在這樣熱烈地希望你去。”他把“熱烈”兩個字說得特別重。“我一般只能通過我所教的學生間接地影響中小學。”
課程改革給他提供了一個求之不得的平臺,讓他到“用戶”(中小學)那里去尋找源泉和動力。
他的“科學探究性學習理論與實踐研究”,就是在這期間得以更快地切入課堂的。
“要培養一個人的能力,必須讓他有機會領略別人是怎么想問題的,也就是得出一個漂亮結果的過程。而如果你只是把最后的、最精彩的結果給他,就會讓他產生一個印象:你就是一個天才,只有你才能想到這個。實際上,你經歷的這個過程不也是彎彎曲曲的嗎?而讓他知道這個過程,他就會想:假如我經過這個曲折過程的話,我同樣也能達到目的。所以,科學探究不完全是教人知識和能力的問題,它更能使人有信心!”
這是他到實驗區常說的一段話。因為“科學探究”也是理科新課程的核心理念。他想把科學探究的思想永遠留在他走過的每一所學校。
“這不是雙方受益的事情嗎?我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確確實實感到思想變得越來越深刻了,而不是在吃老本。
“但是,我覺得我們最大的合算、最大的回報,是一種很難得的心靈交流。你確確實實地感受到了互相認同。”
內蒙古烏海市海渤灣區臨近沙漠,經濟不發達,師資條件也很有限。羅星凱和他的工作組去了好幾次。每次都要待上幾天。
“有一天晚上,我們被老師們拉去搞一個沙龍。結果,一開始,他們就問我們的人生經歷,問我們的求學過程,問我們的家庭是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樣。一講到這些東西,我們每個人都動感情了。我們中有好幾個都是吃過苦的,和他們立刻有了共鳴。這樣的心靈交流,讓人感到真的很舒坦。人很有必要體會另一種境界。”
羅星凱的腦海里還一直晃動著兩個場景。
一個是他們每到一所學校,特別是小學,老師們迎接他們時那種興高采烈的樣子——大學教授都到我們這里來啦!——那是怎樣的一種熱望與渴求啊!師范院校怎樣介入中小學教學研究都不為過!
另一個場景,是在他們評完課后臨走的時候,一位教師緊緊握著羅星凱的手,眼淚不禁要奪眶而出——那激動的樣子,令他久久不能忘懷。
羅星凱回憶道,那次不過是進行了一個對話式的評課活動。彼此非常平等,討論很熱烈。但就是這么一點,也讓教師感動成這樣。
“我們越發感到,課程改革,改變的不僅僅是課程。這些平等、民主等文化意義上的東西,真的是可以滲透到人的心靈中去的。”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所做事情的意義。
“我們就是被不斷扔到這個場景中去,不斷考驗自己的態度,是不是平等的、民主的,是不是在身體力行。可是要每個人都在行動中,在每一時刻都滲透這種思想,是最難的。
“好在,我們都學會了反思!”羅星凱如釋重負。
2005年5月,47歲的羅星凱獲得了一項至高的榮譽——“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由國家最高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表彰的“勞動模范”。
“‘勞模’的形象似乎與我這個有點特立獨行的大學老師形象不太吻合。這份榮譽對我來說太重了。但令我特別高興的是,在這份榮譽的評選中,領導和同志們很看重我在基礎教育研究領域里所做的事情。我想每一位參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實踐者也會感到自豪。”
所有的榮譽都到頭了的時候,榮譽也就不再成為榮譽。
但人生還得前行。
他在一份材料里寫下這樣一份獨白:
我一直在為我擅長并真心喜歡的事業尋覓一種終極的動力和寄托,使自己可以盡可能地(如果不能完全的話)超脫眼前的功利追求。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給我們帶來了難得的機遇。2001年我校掛牌成立“教育部廣西師范大學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在有的人看來,也許這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臨時機構,而我卻對它十分珍惜。因為直接指導它的是我們師范教育的“客戶”,它提供的是一個巨大的平臺,使我可以聯手志同道合的同仁,組織感興趣的同事,在那里探尋、實踐著自己過去始終夢想的理想。
(責任編輯:王亞莉)
來源:《基礎教育課程雜志》2005-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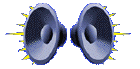 媒體報道三:
媒體報道三:

羅星凱:傾心服務基教
羅星凱,廣西師范大學物理與信息工程學院教授、廣西師范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所長。在教育界,提起羅星凱,很多人都會稱道他服務基礎教育的執著勁兒。長期以來,他在從事科學教育研究和師范教育教學工作的同時,帶領他的課題組從基礎教育改革發展的需求出發,將科學教育研究、持續系統的師范教育課程與教學改革以及服務基礎教育工作相結合,逐漸形成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成果,不僅獲得國內外同行和校內師生的高度評價,而且得到了作為師范教育用戶的基礎教育界的高度認可。
寓研于教 堅持教改創新
師范教育是直接為基礎教育服務的,但在師范院校里,真正致力于學科教育研究及教學改革創新的人并不多。而羅星凱從事的正是學科學法的教學與研究,他那種超脫大學學術評價體系、真正從“用戶”角度定位自己工作價值和方向的執著精神,最為人所稱道。
羅星凱是廣西師大和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屆教學名師。將高超的教學藝術與獨到的教學研究融于一爐,是他倍受學生歡迎的原因。一位名叫唐珩的學生在期末學校下發的教師評課表上這樣評價他的課:“羅老師在課堂上風趣幽默、妙語連珠,既有發人深省的思考,也有新奇輕松的小案例,而最令我們感興趣的就是他對實驗的改進演示……羅老師不僅授予我們知識,更多的是教給我們一種思維的方式和方法,這是終生受用的好東西。”
羅星凱教授的教學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在課堂上不僅善于挖掘諸多耐人尋味的討論話題,還能把深刻的教育教學理論以通俗的方式表達于具體的教學實例中,讓學生們從真實的教學行為中讀懂或領悟那些經典的理論。平日里,他通過細致觀察、獨立思考、與同事學生討論交流,以及對自己的思考進行反思,將一個個平凡的教學事件變成學生專業成長所需要的豐厚的學習資源。然而,羅星凱并不滿足于在教學實踐中的經驗積累和個人教學藝術的提高,他不斷用科學研究來充實和更新自己的教學,探索如何更全面、更有效、更科學地傳播知識。
熱忱投入 服務基礎教育
羅星凱曾在中學任教10多年,對基礎教育有著濃厚的情結,他堅定地認為,基礎教育屬于奠基工程,是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之一。進入大學任教以后,他便熱忱投入到為基礎教育服務中。
在參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期間,他每年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到各地各級的中小學聽課、評課、授課,作報告,搞調研。他所作的專題報告,在中小學教師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他所走過的課堂,總能留下耐人尋味、讓人為之折服的東西。一次,羅星凱和數十位教師在一所中學觀摩實驗課,實驗非常成功,學生對現象的解釋也沒有困難,在觀課老師表示滿意的情況下,羅星凱卻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了實驗的不足。他的語氣雖然平和卻一針見血,句句說到教師們的心坎上,說得大家都很服氣。
隨著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深入,廣西師范大學形成“基礎教育課程與教學研究及其人才培養”創新團隊。在首席學科帶頭人羅星凱的帶領下,團隊積極面向基礎教育開展研究,經常深入中小學教學一線提供理論支持和幫助,也挖掘到大量生動的教學案例,發現許多可以深入研究的問題。他們把這些案例帶回大學課堂,實現了教師教育小課堂與基礎教育大課堂的有效溝通;把發現的問題深挖下去,就是極具價值的科研課題。如今,該團隊在科學教育研究方面形成了服務基礎教育的鮮明特色,他們正承擔著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項目綜合類課題“科學探究課程的設計與實驗”的研究。
科學探究 要讓學生參與
經過多年的教學和科研實踐,羅星凱逐步形成了一套獨到的科學探究理論。如今,羅星凱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國家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實踐中被推廣應用。
課程改革較早的上海市,率先使用了羅星凱的項目成果《中學物理疑難實驗專題研究》教材。上海市教委認為,羅星凱的這本教材為廣大中學教師提供了一本難能可貴的教學參考書籍,為幫助教師解決物理實驗中的疑難雜癥提供了新處方。
同時,羅星凱的“科學探究活動設計和案例開發”成果也為基礎教育新課程實驗及其教師培訓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和有力的學術支撐。如他和廣西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的專家們經過多年努力,建立起了“迷你科學探究館”。這是一個基于校內、由師生共同參與建設的小型科學探究館,為學生提供探究性學習的開放性實驗活動基地。雖然該館的氣勢和規模無法與校外大型科技館相比,但它具有門檻低、參與性和教育性強、內容活且改進快、給師生的親近感強等特點。中國工程院院士韋鈺、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澤、法國科學院院士依維斯•蓋雷(YvesQuéré)和皮埃爾•雷納(PierreLéna)等專家都曾到“迷你科學探究館”考察指導。他們認為“迷你科學探究館”里的探究實驗雖然小,但很有意思,應用于科學教育將非常有價值。如今,該館的建設模式和特色已經面向基礎教育積極推廣,湖南長沙八中、內蒙古烏海海勃灣第三小學等一些中小學相繼建立起了自己的“迷你科學探究館”。
來源:《中國教育報》2008年2月17日第2版